
夏至将至,九年了。
河南周口商水县平店乡田野的日头,在夏至前便显出几分狠劲来。清晨五点钟,天已大亮,阳光穿过杨树叶的缝隙,在黄土院子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母亲总是这个时辰起身,我听见她趿拉着布鞋走过堂屋的"沙沙"声,接着是挪开水缸木盖的"吱呀"一声。她先舀一瓢清水净了手,而后灶屋便响起锅铲相碰的清脆声响。
她的围裙是蓝底白花的,洗得发白,腰间用一根布条松松系着。灶台是用黄泥夯实的,经年累月的烟熏火燎,表面结了一层黑亮的釉色。她蹲下身去,往灶膛里塞麦秸,火苗"呼"地窜起来,映得她半边脸发红。铁锅里的水开始冒泡时,她便把昨夜发好的老面倒进陶盆,手腕一抖一抖地揉着。那面团在她手掌下渐渐变得光滑,像婴儿的肌肤般泛着柔光。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做手擀面的样子。案板是槐木的,用得久了,中间凹下去一个浅坑。她把醒好的面团摔在案板上,"啪"的一声闷响,接着便用那根枣木擀面杖来回碾压。擀面杖两头细中间粗,被她手掌摩挲得油亮。面团渐渐摊开,她不时撒一把玉米面防粘,面粉在阳光下纷纷扬扬,像细小的金粉。最后面皮能透光时,她便将其叠成几层,菜刀起落间,面条便如银丝般垂落案头。
夏至前三天,她必定要蒸几笼馍馍。蒸笼是竹制的,边缘已经发黑。她垫上洗净的玉米叶,把揉好的面团排进去。灶膛里的火要烧得均匀,她时不时用火钳调整柴火的位置。蒸汽升腾时,整个灶屋云雾缭绕,她的身影在其中时隐时现。馍馍出笼时白胖可爱,她总要拿一个在手里左右端详,像欣赏什么珍宝似的。
菜园里的苋菜这时节最是鲜嫩。清晨的露水还没干透,她便挎着竹篮去采摘。苋菜叶上沾着细小的水珠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她掐断嫩茎时,紫色的汁液便渗出来,染在她的指甲缝里,要好几日才能褪净。回来洗净,焯水后拌上蒜泥,盛在青花瓷盘里,那颜色绿得几乎要滴出水来。
夏至那天,她天不亮就起来熬绿豆汤。绿豆在铁锅里翻滚,渐渐绽开白芯。她撇去浮沫,加一把冰糖,盛在瓦罐里用井水镇着。晌午最热时,我们满头大汗地从外面跑回来,她便从水缸后头端出瓦罐,绿豆汤已经结了一层薄冰。我们咕咚咕咚地喝,她就站在一旁摇着蒲扇,嘴角微微上扬。
如今又是夏至将至。我在远在他乡超市冷柜前徘徊,那些包装精美的速冻食品整齐排列,却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味道。厨房里的案板光可鉴人,擀面杖是新买的,还带着标签。我试尝试着,却怎么也找不出那种柔韧的质感。
去年回老家,看见她用的那把铁锅还挂在灶台上,锅底结着厚厚的黑色锅巴。我伸手摸了摸,指尖立刻沾上一层黑灰。院里和一层屋顶的菜园早已荒芜,只有几株野苋菜在砖缝里顽强生长,开着不起眼的小花。
夏至的阳光依旧灼热,穿过破旧的玻璃窗照进来,在地板上投下的光斑。我忽然想起她总爱在这个时辰把棉被抱出去晒,说这样晚上睡着有太阳的味道。如今我的衣柜里塞满了各种香包,却再没有那种阳光的温暖气息。
九年了,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成人,却不够冲淡记忆里的那些细节。我至今记得她低头尝汤时,一缕头发垂下来的样子;记得她擦汗时,用手背抹过额头的动作;记得她笑时,眼角浮现的细密纹路。
夏至将至,我想给她捎点什么。最终只是煮了一锅绿豆汤,任其在冰箱里慢慢冷却。汤里浮着几粒没煮烂的豆子,喝起来有些涩。这滋味,倒像极了思念的滋味——总是差那么一点火候,永远不够完美,却偏偏叫人念念不忘。
夏至将至,远在天堂的妈妈,父亲,不知此时此刻的夏至是不是如 人间那般灼热,愿儿女的思念给您们带去一丝丝清凉......
liutong 2025N6Y19R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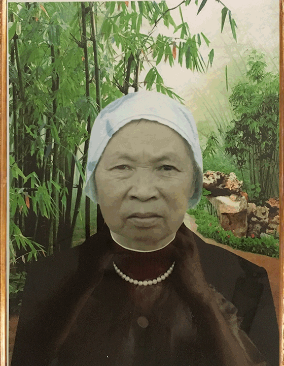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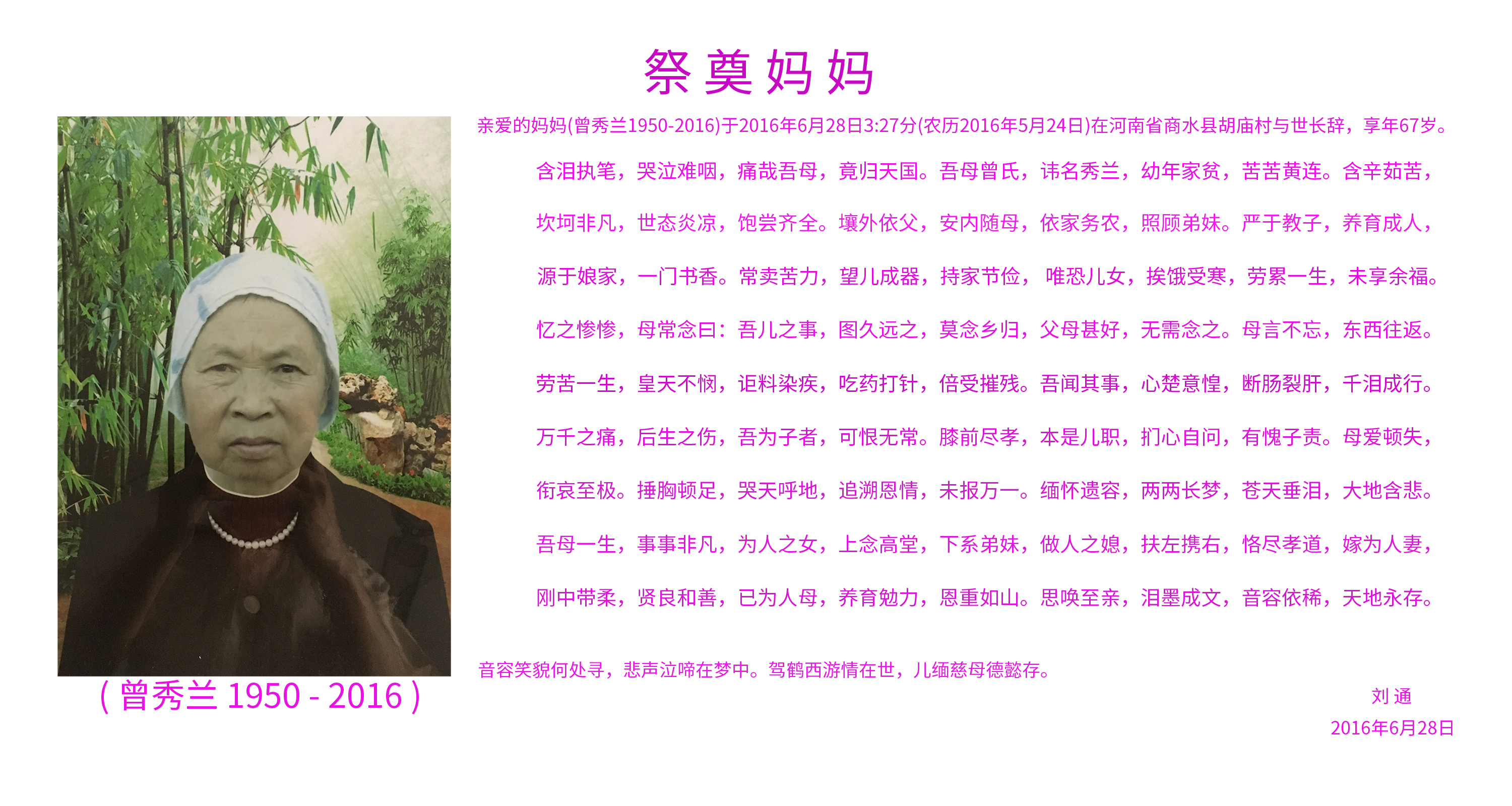
评论一下?